画画这个事对于我来说从根上讲纯粹就是捡来的事。我不定干什么呢,结果就画画了,而且自己还喜欢。因为学校是放弃你的,家长对你也不自信。我觉得家长都有武断的一面,有的家长特别好,很民主,让孩子自己发展,或者给你很大的引导。每个家庭可能都有很奇怪的一面,和别人家庭不同的一面,它会给孩子的心理上带来一个直接的影响。但家长他们不在乎他们活得很自然。他们觉得给你吃给你穿,给你上学的钱,冬天不会让你冻着,夏天不会让你热着,就没问题了。但是实际上这里面问题特别多。我爸爸是从农村出来的,当兵嘛,在家里老大也不太好好干活,他就是被打出来的,就对他造成一种惯性,他要打孩子。我经常因为学习上不太对他的路子而挨打,经常的小时侯。每一次他打你都觉得是应该的,而且在这整个过程中,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,补偿他自己挨打的那种感觉。当时我觉得他很愉快,打你的时候准备特别充分,你又不能离开那个屋子,得等着,酝酿到极限时候,他觉得火候够了,就开始打。有的时候也偶发,就是逮住了在院子里一顿踢,他挺爽,一看表还有个会,走了。后来我就逃学,我爸就捉。一个军属大院,我爸那时三十几岁,根本跑不过他。你就紧捣,几步他就过来了,一拎脖子一脚就踹过来,那时侯特别小,一年级。第二年夏天,有一天跟一帮小朋友玩,突然就跑不动了,腹部特别疼,就到县医院去检查,有一肿块。后来又到长春一个部队医院,医生说可能长了个东西,要做手术。做手术头一天要做一个穿刺,取里面的液体。来了七八个医生把我摁在床上,拿一大针头,做一个穿刺,一化验说没事,是个瘀肿。那医生我印象特别深,一军医,灰白头发那种感觉特别慈祥,就过来跟我爸说:你是不是打他了?你是不是老打你小孩?我爸就不好意思,就乐,他在外人面前特别弱。我看我爸那表情,他在说谎。我觉得我特委屈,就在那儿哭。不用做手术,吃点化瘀的药就行了,开了很多药。第二天我爸就带我去了一个饺子馆,机器压的饺子,和扎啤,那是第一次,74年。我爸要喝,要了两扎,我说我喝不了,他说少喝点,倒碗里,喝了几口,吃那饺子,觉得特别好,觉得我爸对我挺好。我小时侯经历了很多这种疼痛的感觉。
家里是我哥先画的,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觉的艺术家。他喜欢这个,早期的命运也比较好,因为我妈支持他。我们小时侯他们夫妻俩有一种分工,我妈管我哥,我爸管我,说不清楚的一种分工。我妈很宽容,对我哥只要学习好干什么都行,喜欢无线电呀,喜欢画画都行。但我小时侯是什么爱好都没有,就是想玩,不想在家呆着,就想出去玩。不喜欢幼儿园,不喜欢学校,所有被管的地方都不喜欢。也不是愤青,小时侯属于那种很内向的孩子,很懦弱。家里面那种教育给你造成一种奇怪的影响,心里很压抑。我爸管我,他觉得有权支配我。上学的第一天我就觉得我没法进入那学校。所有的男孩都背军挎,给我买了一个花书包,还是那种两个带子拎着的,白底黑花的。书一放进去是软的,不像军挎那么有型,那样斜挎着就去了。然后给我剃了一个锅盖头,我自己不知道。我爸说了:你头发长了明天要上学,今天给你剃头。我最讨厌剃头了,后来就一直希望留一长头发。把我摁到过道里,直接一圈儿,可能现在看挺时髦的。整个一圈是光的,上面顶一盖儿,还是一大盖儿。一照镜子我就哭了,怕挨打,算了,别哭了。第二天顶着那个就上学去了,一进班人家一看这孩子真惨,整个一滑稽。我妈也不满意,我爸就坚持:就这样,挺好。
有天和邻居孩子打架,把人给打了。那时侯我们家已经从东北到了太原。我爸那时侯已经有病了,但还天天上班,特硬朗,有条腿不行了。我还在上初二,肯定不敢反抗家长,打你白打。我哥已经上大学了。那天家长带着孩子告到家里来了。我爸就习惯性地把小屋门关上了,从后门抽出一根擀面杖。我一看要搞事。因为屋很小,有一写字台,里面有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双人床。我就往里躲,穿着鞋,又不能踩着床。当时心态很复杂,我妈爱干净,我爸又要打我,没地方跑了,只能往床上躲。躲在床上两脚支起来,搞一造型准备招架。我要是搞雕塑,我就搞一造型,叫“挨打”。那种李连杰飞腿,等着。我爸就先乐了。他愤怒就愤怒在这儿,觉得我太老练了,太有经验了。腿支好以后,我爸就急了,过来以后就“你妈的……”。怎么打也打不中要害,腿在踹嘛。他打的时候还摁着打,不是一下一下打,打空当,有一种技巧在里面,总之得够到一个要害。我一看这不是长久之计,一个翻身,床单也踩了,直接站起来就跑了。我爸回身很牛×的一下子直接打到膝盖上,一头就栽下来了,趴在地上,后背还继续挨着打。我妈在那边也听见了,过来就说完了完了,你这不打断了吗?打可以,我妈同意打,打断了我妈就急了,把擀面杖往下揪。我爸说你别管,那种山西土话。我就抱着腿使劲叫唤。这会儿我一个哥们儿来了,特别好一哥们儿,叫小光子,现在已经死了,吸毒死了。那会儿玩得特别好。他来了就说叔叔别打了,问我怎么了。我就说腿完了,肯定断了。他就背我去了分局厂医院,照了一片子,膑骨打裂了。就上不了学了,没法走路了,开了药在家呆着。呆着干嘛呢?平时爸爸老逼着我学习,这回说打的特别重就没逼着我学习。我就翻电影画报,那时侯已经有《大众电影》杂志了。我记得是《爆炸》呀还是罗马尼亚一电影女明星放的挺大的,挺漂亮的,黑白的。我就拿我哥剩下的炭笔和纸画那个女明星。就觉得画的挺像的,我觉得是宿命的一种真实吧,确实安排你在那个点做那件事情,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这样的。后来又把我哥剩下的一块三合板拿来了,学他那种感觉。记得中学课本上有一课《老人与海》,我就把那个鱼网和罐子刻出来了,又画了一张。这时候我妈就进来了,哦,你也喜欢画,学学你哥吧,你都这么大上初中了,将来你要干什么,接你爸爸班吗?我也没说话。我妈就过去跟我爸说:小永呀也喜欢画画,你以后别打他了,好好培养培养他,看他能干点什么,反正学习也不太好,学习不好能画画也行,考个中专也行,只要不出去惹事就行。后来我就真的开始画了。翻我哥剩下来的书,把那些翻出来画,就真的不出去了。以前天天想尽办法出去玩,不愿在家呆着。我们家住一楼,厕所窗户这么大,小方窗。每一次出去玩都从那儿逃跑,因为开大门的话我爸会听见,但你说你去上厕所,就没问题。每一次逃跑都是从厕所跑。家里不知道你跑哪去了,也不知道你怎么跑的,没听见动静就跑了。这种经历过来了,我觉得跟家长对你的要求有关系,所以现在我有了孩子以后,我就尽量不压抑他。我觉得是压抑的结果,是家长给你造成一个压抑的环境。他是跟普通中国家庭一样的,他希望你好,但他使用的方式是一种很主观的方式。我看我爸那种感觉,他早期读私塾,考了县里面的中学,他小时侯就是被老师打出来的。上了高中以后我奶奶给他定了一个亲,高中就可以结婚了,那是刚解放的时候。他是这么过来的。我奶奶特别不喜欢我爸,他属于那种也是被压抑出来的。他人很喜欢读书,我奶奶老说你爸爸学习好,其实这在农村是最被看不上的。天天抱着书看,不干活,也不会干活。他是从那种家庭出来的,被压抑、被打出来的,后来就开始打我。
考学的时候当时是先考中央美院,特别想上。后来浙美这边的准考证也寄过来了,要求到杭州去考。从来没出过那么远门,家里面凑的钱。当时山西只有两个他们的准考证,我哥们儿那儿有一张,我们俩一块儿来的。我考完中央美院以后,中央美院每年要招附中的人,外面的学生除非你基本功特别过硬的才能进去,全是内定好的,剩下的名额就没几个了。后来去浙美以后,变了一种方式,现代画,勾线的伏尔泰,我印象特别深。学生那个高考指南上考生作业里有一张一个线的侧面,那就是我画的。当时浙美考的成绩不错,中央美院没考上,反差特别大。
我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,当时想之所以好是因为注意了别人没注意的问题,而不是说你有多大的本事。你就是因为注意了别人不注意的东西,这个是我那时有的感觉。因为我们在浙江美院当时大家的注意力就一种,来大学就是要把我们的功夫练好,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。或者我们要练好基本功,我们的天地是毕业以后的事。我不是,因为我哥告诉我,开始就要进入一个创作状态,不要把它完全当作一个过程,那样是不对的。你要画每个东西都要当一个东西去画,这当时很多同学没有。
2
刚一来工艺美校工作,我操,不对呀,后面全是菜地呀,跟你印象的北京是两个概念。实际上刚来北京是不安,后来由不安转成烦躁。这是什么地方?郊区呀!马车,骡子车,农民,三轮车,马拉的屎……这哪是北京呀?特绝望。基本工资80元钱,加上上课,100多一点吧,很少的钱。当时借了2000元,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债了。一张画也没卖,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吧,接到老栗一封信。我现在还记得那封信的内容,特别短。“宋永红你好,看了你们两人的画展,很激动,尤其是你的画。你会越画越好的,多多努力。”我操,这他妈是老栗写的信呀。我说这是老栗写的呀,旁边好多同事就说,老栗是谁呀?我说“老栗……不知道”。当时是在一个老师那儿,有一个黑白电视,大家都在那儿看《渴望》呢。拿到那封信,我特激动。看完《渴望》回去又接着画,真是那种特别激动的感觉。
后来因为有一点钱嘛,你要做工作室的话,你就没有机会买房子,买了房子就没有工作室。就这么多钱,怎么弄?那我第一反应就是肯定要弄工作室。老婆就不干了,人家跟你图什么呢?彩电也有了,家也有了,在家里呆着,小空间怎么弄,这很具体的。我就觉得挺矛盾的,也没法解决,很多画也卖得不好。如果钱很多的话,也就不是问题。至少你解决空间的话很容易,但是很多原因就积在那儿你弄不出来了。而且画画非常非常觉得没劲,我操。不是说你不想画,你不知道画什么。我操,画什么鸡毛呀,完全是乱套的。然后每天我那儿还有一些册子,这个展览,那个展览,通过各种途径吧,别人还会打电话,让你去看展览,然后给你册子。别人来看你呀,带册子,很多东西跟你所看到的是不同的。就你在画,就你画的刁毛东西别人都知道。就说一打电话说:永红,找你,去你那儿玩,怎么样?电话一放就知道你在干嘛,太清楚你的东西了。你也知道对方是这种感觉来的,特别清楚这种感觉,又特别无奈吧。我哥也来一块讨论这些东西,他谈不清楚。
我来花家地呢,首先一点,你也知道我当时在国内的状态。我刚从美校出来,然后老婆生孩子,我心情特别不好。所以当时我从美院出来以后,种种原因,我就他妈的,我太不适应这个社会了。这种性格也是从小养成的,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应社会的。现在才知道,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种方式切入它。你在一个环境里面,你首先要找到一个方式切入。我本来不是理性做事的人,所以混乱经常伴随我,混乱时间的长短要看你的运气。如果偶然的一个机会你碰开了这个锁,那你就开始调理了,调理才开始工作。或者碰见一个人、一个事。但我到鼓楼那儿的时候,就跟整个环境都脱离了,你跟谁都……。
我是喜欢扎堆儿,我不骗你,我特别喜欢热闹。就我这种性格来讲,一个人呆时间长了就死定了。我喜欢热闹的方法还是喜欢和大家住在一起,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。但是这么多年在北京,一直找不到这种机会,你摆脱不了。当了七年的老师,那些分配过来的老师,你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也得住在一起,大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也能弥补缓冲一下那种想要群居的感觉,但是不是那些你最需要的朋友。所以这次花家地这儿,有这样一帮人,很多年的想法,大家想法一样的。有一种愿望,在一起既可以玩也可以说艺术。现在好多人都不再谈艺术,只谈经营,谈怎么经营或经营的方式。有一个哥们儿谈到现在的现状有一个比喻,就像鸭子游泳,上面不动,下面乱动。现在就是这样,底下操作,上面看那鸭子很安详,没什么表情,但底下的脚紧捣。
昨天跟老栗说到一点,我是在画和我自己有关系的一个东西。你像刘炜、毛焰那是属于手感一流的画家,他们属于典型的那种很有才气的。但我觉得他们不太管是不是和自己生存有太大关系,我是说现在,以前不这样。从前我看过刘炜的作品,他画他父亲,他画电视、戏剧,他画鸟,画那种孩子、那种山,他有一种和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东西,或者和(生活)背景有关系的东西。后来画的肖像就是一种纯粹语言的感觉,那种稀巴烂、稀汤逛水的感觉。我觉得他的兴趣在于画面本身的那种东西,不太管背景怎么样,就管把一张画画好,也许是我的一种理解吧。画一个肖像,就传达这个肖像的情绪。当然我也不太直接去联系、翻版我的这个生存的现实,但我觉得我是有感而发的,和我生存的这种感觉是相联系的。
我喜欢的画家挺多的,包括怀斯,包括达利,我很早就喜欢具象的东西,对抽象的东西没感觉。不是说不喜欢,我感觉不到那种抽象手法的东西。我可以看到抽象的好画,可以看表现主义那种感觉,那种特别牛×感觉。但是同时你觉得你不是一个欣赏者,你要做。你要做一种有知觉的东西,我喜欢有形的东西,喜欢表述清楚的感觉。那种清楚不是为了叙述,而是传达一种感觉。因为我们每天一醒来看到的是形象,而不是没形象的东西,我相信这种直觉的东西能让你激动。
画在背后流的水,凝固了,所以我才这么画。不是大卫·霍克尼,也不是古代的洗澡,所以我画这样凝固的水。同时我也觉得一个人成画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的。老栗也谈过所谓“原创性”,很多人就是苦恼、苦恼,苦恼在一种原创性。你要找到一种原创性,好像别人都没做过,是我第一个做,彻彻底底、干干净净,所有所有东西都是我第一个来弄的一个原创性。很多时候抛开原创性,然后我们找一个感觉的时候就容易了。我们可以使用任何一种语言,只要有感觉,它就存在。因为我们不是开天辟地呀,而是永远的机会,永远呀。但是我们是有感觉的,我们找到我们的感觉就容易了。如果你要找原创性那就歪了,屁!什么原创呀,人身上下没有原创的。你父母生了你,你身上的衣服,你住的房子,你他妈的学习的东西全是原来的,但你唯一剩下的就是你的感觉。后来我就一下觉得,你这种感觉是无标准的,你的“主观性”是主要的,指导你。所谓你的“主观性”就差不多是瞎整的东西出来,你怎么样把它弄出来都是对的。你的“主观性”就是你定它是什么,它就是什么;你怎么画它,它就是什么,那就对了。而不是还有什么标准,没有标准,一下就自由了,这个特别重要。我有,我从来就有。我二年级、我考学一瞬间的那种感觉,然后包括整个过程,我觉得我有。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丢掉了,我怀疑了,我偏离了。我找一种别人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的时候,我偏离掉了。我觉得一下就解开了自己,所以让我兴奋,所以我觉得是个宣泄的过程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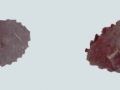

 豫公网安备 41010402002371
豫公网安备 41010402002371